1
荀子,生卒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享年很高,应该有 90 岁以上。尝游学于齐之稷下学宫,至齐襄王时“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惜乎齐襄王不能用,且见逐。遂居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见废。于是,著书立说,遂有《荀子》一书 32 篇。
2000 多年以来,《荀子》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不断有学者阅读与研究。
荀子与孔子、孟子并称为先秦三大儒者,但我们一般把孔孟之道作为儒学的代称,而没有加上荀子。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孔孟之道代表了儒学的正宗,这个正宗就是由内圣以至于外王,但荀子则隆礼重法,对于内圣不甚措意,而特重外王。这样,荀子的社会理想以至于对于人之境界的开发都显著地异于孔孟。一般以为,这个差异的根本点是孔孟主张性善,而荀子主张性恶,这是根本的误解。其实,荀子理论的中心是天人关系。
2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荀子》一书,这里着重说一说荀子的以下思想:天人观、性恶论、心论、隆礼重法、明分使群。
第一,天人观。本来,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孟子那里,天与人是相通的。故孔子讲“知我者,其天乎!”孟子亦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荀子却与之不同,大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在荀子那里, 天就是自然之天,非孔孟之道德性理之天。天功一方面强大,另一方面神秘。然无论强大也好,神秘也好,总是天之事,与人无关,因为人没有办法改变天之规律。这是圣人不求知天之意。所以,荀子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宣称不要太在意天之所为。天的运行规律虽不能人为地改变,但可加以利用,以为人类造福。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 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荀子强调自然之天的客观性,而不与人之道德相关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对的。但荀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他完全没有看到先秦以来在自然之天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道德宗教之天,这个天则与人的道德有关, 一切对人或人性的认识必须关联着这个道德的天而言,可惜荀子完全以自然之天取代了道德之天,使得他接不上孔孟的正宗理路,开出了儒学的别支。荀子的性恶论及隆礼重法之思想,俱为其天人观所衍生,虽然于孔孟的正宗理路有所创发与转换,但毕竟是儒学的别支。本来,儒学在孔孟那里是教,但在荀子那里,儒学不再是教,而只是学了。

第二,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性恶》篇的中心思想,在文中反复出现。这里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人性根本为恶;其二,通过后天的教化,人可以为善,这就是所谓的“化性起伪”。
荀子为什么说人性是恶的呢?他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这些都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谁也不能否认。如果人类任凭这个本能发展下去而不加以抑制, 则诚如荀子所言,“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这根本是禽兽而不是人类社会。因此,荀子认为,人类社会要善治就必须正视这个恶的本性而加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从而使本性为恶的人做到善。
荀子斩断了人与天的关联,只看到人的生物性之存在,从而力主性恶论,这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他由此而完全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却是学有未达。实际上,孟子并非不承认荀子所言,且其陈义更高。孟子看到了荀子所看到的东西,但荀子没有看到孟子所看到的东西。是以在对人性的阐发上, 荀子较孟子毕竟差一筹。
荀子主张性恶,看到了人性消极的一面,从而欲矫正这个消极的一面, 于是,重视外在的礼义法度,从而把人提升到“涂之人可以为禹”之境界。但荀子达到这个境界靠的是外力而不是自觉,蕴含着走向暴力与专制的危险,后来其弟子韩非与李斯完全走向法家,正是这个原因。
第三,心论。在孟子那里,性是虚说而心是实说。孟子主张性善,但性善到底是什么呢?要落实下来,性善实指四端之心,外此四端之心,无所谓性善。故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心与性并无质的区别。但在荀子那里,性是实说,乃人的生物本能,心亦是实说,心与性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么,在荀子那里,“心”到底是什么呢?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荀子·解蔽》)
荀子言心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也是大体之意。即心是出令者而不是受令者,心有自己的潜能与自由,所谓“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 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要求心应专一而静,若博杂则必乱,而难以 知“道”。故荀子盛言解蔽,且认为“虚一而静”之心才能知“道”。
荀子之所谓心具何特质?它似乎就是一个虚空的大容器,里面空无一物。虚一而静就是把心打扫干净,呈现其本有之虚空,不让异物与杂质占据, 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大清明”。这样一个大清明之心方能知“道”。不然,若以“已臧害所将受”,必不能知“道”。荀子之心论类似于西方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人心只是空无寥廓之容器。这样,荀子析心与道为二,不似孟子,心非白板而具四端之能。

第四,隆礼重法思想。由荀子的性恶论与心论必至于隆礼重法。荀子因秉持性恶论,他不可能认为礼之生乃基于人性,恰恰相反,礼是要矫正人性的,礼完全是圣人之伪,即外在制作。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礼乃起源于人因欲望而来的纷争,先王必须以礼加以限制而归于治。尽管荀子也讲“礼者,养也”。但其所谓“养”非外在的扩充而养性之“养”。荀子把礼义之养情、养安而与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之养威同理看待, 说明其养是外在的。即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使人显得很有威严。同样,礼义外在地使人显得有情谊,安而不乱。如果人人基于礼义而不是性情, 那么,人人安居而社会和谐。
正因为如此,治理国家必须隆礼。基于此,对于人而言,学习主要是学礼,而非《诗》《书》。故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又曰“: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陋儒、散儒都不是好的评价,不知治理之大道仅知晓文章典故而已,其根本原因在于不隆礼而顺《诗》《书》。

第五,明分使群。在荀子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绵延而强大,就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以礼组织起来的群体;君主就是善于治理这个群体的人: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荀子·君 道》)
但是“群”并非指群体内的成员平均齐一,而是要有差别的,故群体之所以能被组织起来,关键在于“分”。“分”靠什么来体现,就是依据礼。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
义者,宜也。宜就是界限分明、等级有序、贵贱有差,也就是“分”,这就必须依靠礼来体现。
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礼作为一种“度量分界”,使得群体有客观的仪轨与规范可循,从而保证了政治社会的客观性,使人民各尽其职而社会富足、得到善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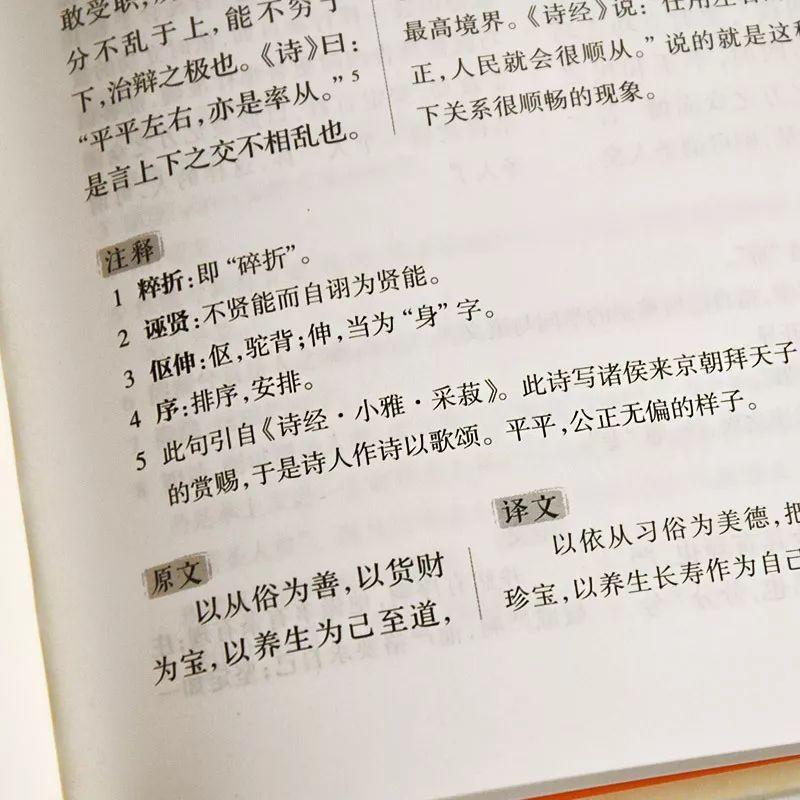
在《荀子》一书中,“礼”字随处可见,它规范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荀子将“礼”的内涵与具体的“周礼”区别开来, 并将之提升为“知识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概括起来,礼的作用如下:
其一,在个人层面,礼是人的基本生活规范与教养的标志。
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荀子·礼论》)
其二,在家庭层面,礼是齐家的基本方法。
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 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荀子·君道》)
其三,在社会层面,礼是经济富足、分配合理的基本依据。
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 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
其四,在国家政治层面,礼是君主、臣下依法行政的基本保证。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 忠顺而不懈。……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正因为礼关涉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诸多层面,故礼之于人特别重要,起到了“表”治乱的作用。
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表天下之乱。今废礼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荀子·大略》)
礼既然如此重要,教化即在此体现,人的学问的成就也在礼处体现。




















